新笔下文学 www.xxbxwx.net,灶神之凄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每当我母亲跟我说话,一开头总像跟我吵嘴似的。
上星期她打电话给我,劈头就说,"珍珠啊——你非去不可,没二话好说的。"好大一会,我才明白她打电话的原由:海伦舅妈邀请一家子去参加我表弟宝宝的订婚晚会。
所谓"一家子"指的是匡家和路易斯家。匡家有海伦舅妈、亨利舅舅、玛丽、弗兰克,再加上宝宝。而路易斯家呢,现在实际上只剩下我和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去世了,而我弟弟塞缪尔现在新泽西。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别人就把我们看作"一家子",尽管匡家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海伦舅妈的前夫是我母亲的哥哥,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去世了。
说起我的表弟宝宝,他的本名是罗杰。但从小全家就叫他宝宝——宝宝在中文里是"乖孩子"的意思——后来就这么叫开了,因为他是个哭宝宝,我舅舅和舅妈一进门,他就哇哇大哭,说别的孩子惹他。现在他虽已三十一岁了,大家还是拿他当小孩看,还是要惹他。
"宝宝?他怎么又开订婚晚会了?"我说,"这是他第三次结婚了吧?"
"第四次了!"我母亲说,"上次没结成,我们送礼后不久就吹了。当然,这次海伦没说是订婚晚会,她只说是为玛丽搞一次大团圆。"
"玛丽也来了?"我问道。玛丽和我不光是表姐妹,还有另一层关系,她嫁给了杜楚,杜楚是我丈夫菲力勃兰特在医学院里的同学。说起来,十六年前,我和菲力还是经她介绍才认识的呢。
"玛丽要来,她丈夫和孩子们也来,"我母亲说,"下星期从洛杉矶直飞这儿。来不及买优待票了。买全额票,想不到吧?"
"下星期?"我一面说,一面找着借口,"现在通知我们临时改变计划好像晚了点,我们本来打算去——"
"海伦舅妈已经把你们算进去了。在水龙饭店设宴——要摆五桌咧!你们要是不去,一半的桌子都要空着了。"
我想象着海伦舅妈那样子,又矮又胖,缩得只有桌子腿那么高了。"另外还有些什么人去?"
"多着咧,都是些大人物。"我母亲说"大人物"这几个字的口气,好像在提起她不喜欢的人。"当然,她也会告诉人家说宝宝和他的未婚妻也要去。于是大家就都会问她,'未婚妻?宝宝又有新的未婚妻了?'然后,她就会说,'噢,我倒忘了。本来是想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的。可别说出去哟。'"
我母亲哼了一声。"她就是爱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这事。所以呀,你得带上一件礼物,也给她来个惊喜。上次你买了什么?"
"给宝宝和他的那位女生?我忘了,大概是一盒糖果。"
"他们吹了以后,他有没有送回来?"
"好像没有。我记不得了。"
"瞧!这就是匡家人的作风。这次可别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宴会前两天,我又接到了母亲打来的一个电话。
"听着,现在要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听她的口气,好像我犯了什么过错似的。然后她告诉我,杜姨婆去世了,享年九十七岁。我对这个消息倒并不感到惊讶,我还以为她早就去世了呢。
"她给你留了些好东西,"我母亲说,"这个周末你可以来拿走。"
杜姨婆实际上只是跟海伦有点血缘关系,是她父亲的同父异母姐妹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但我记得,是我母亲一直来在帮助照料杜姨婆。她每星期帮她清一次垃圾;每当收到印着老太太姓名的"百万美元"赌金独得券时,她就劝老太太别上当去订那些杂志;她还一次又一次地跑加州医药卫生当局,为杜姨婆申请老年医药费补助。
多年来,我母亲总是向我抱怨,说海伦不干这些事,倒要她来干。我母亲老是说"海伦,她呀,甚至提都没提起"。有一次,——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打断了她的唠叨,我说,"你干吗不踉海伦舅妈说你烦透了,而不再跟我唠叨呢?"这是菲力教我说的,以这种合情合理的方式,让我母亲明白究竟是什么使她活得这么累,以便她采取断然行动。
我这句话一出口,我母亲竟呆住了,她一脸惘然,哑口无言。打那以后,她再没向我唠叨过。事实上,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她没跟我讲过话。后来当我们之间又开口说话时,再也没提起过杜姨婆。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以为杜姨婆早就去世的缘故吧。
"那是怎么回事?"听到杜姨婆去世的消息,我尽量用平静中带点震惊的口气问,"是中风?"
"是车祸。"我母亲说。
显然,杜姨婆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精力充沛、身体康健的。出事那天,她当时搭乘的1号加州公共汽车,为了闪避一辆我母亲称之为"一群疯小子驾驶的改装高速车"突然打出的停车信号灯,而倾翻在路边。杜姨婆一个趔趄,倒在座位中间的过道上。当然,我母亲马上赶到医院去看她。医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只发现一些擦伤的青肿块。但杜姨婆说她来不及等医生来找出她早已知道的毛病,于是要我母亲写下她的遗嘱,吩咐后事,那张用了三十年的有节子的沙发给谁,黑白电视机给谁,等等等等。就在当天晚上,她死于未经查明的脑震荡。海伦本打算第二天去看望她,但已经太晚了。
"宝宝罗杰说我们应该起诉,要求赔偿一百万元。"我母亲说,"你想得到吗?动这种念头。杜姨婆临死的时候,他居然不哭,还想从死人身上赚钱!哼!我干吗还告诉他杜姨婆给他留了两盏灯?也许我该故意忘了这事。"
我母亲停了一会,又说:"她真是位好太太,已经订了十四个花圈。"然后她又放低声音说,"当然,每个都给八折优惠。"
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在唐人街罗斯巷合开了一家"丁和花店"。她俩是在大约二十五年前动起做卖花生意的念头的,当时,我父亲刚去世,海伦舅妈又丢了工作。花店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弥补天灾人祸的一个梦想。
我母亲用第一华人浸礼教会给的一笔捐款做花店的本钱,我父亲生前是该教会的本堂助理牧师。海伦舅妈用的是她在另一家花店工作期间的积蓄,她是在那家花店学会做卖花生意,又是在那里被解雇的。海伦舅妈自己说,她是因为"太老实"而被解雇的。但我母亲猜想,海伦舅妈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老是替顾客省钱,劝他们买最便宜的花。
"有时我真后悔婚后进入了一个中国家庭。"菲力听说我们不得不从圣何塞的家中出发,去远在百里之外的旧金山,而且逢周末足球赛交通更加拥挤时,便忍不住这样说。尽管婚后十五年来,他渐渐真诚地喜欢上我母亲了,但对她的不少要求还是有些恼火。再说,从医院下班后与一个大家庭共度周末,决不是他喜欢的度假方式。
"你是说我们非去不可了?"他心不在焉地说,一面忙着玩一个刚装进他的笔记本电脑的新软件。他按了一个键,"成功了!"他对着屏幕喊道,手舞足蹈起来。菲力今年四十三岁,他那一头粗硬的灰色头发往往使人感到难以接近。但这会儿,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一个正在玩玩具战舰的小孩。
我假装也正忙着,埋头啃一段难懂的文章。三个月前,我在本地学区得到了一个治疗语言障碍的门诊医生的职位。我对这份工作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但同时又暗暗担心可能错过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念头都是我母亲塞进我脑袋的。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她,说我战胜了另外两个申请同一职位的人而被选中时,我母亲说:"两个?就两个人要这份工作?"
这时菲力从电脑上探起身,留心我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在担心我的多发性硬化症,我们把它称之为我的"健康状况",这病虽还没有到使我全身虚弱的地步,但使我动不动就感到疲劳。"这个周末将会过得很紧张,"他说,"再说,我觉得你也受不了你的表弟宝宝,更何况玛丽也要去那儿。我的天,这下可好了。"
"嗯。"
"那么你是非去不可了?"
"嗯-哼。"
他叹了口气。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结婚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有关我的娘家、我的责任的话题。因为我们的争吵往往是由这个话题引出的。我们刚结婚的那会儿,菲力老是说我无论干什么总爱盲目地担心和内疚。我则反唇相讥说他自私,我说,人活著有时总得干一点不痛快或不方便的事。然后他就说,我们非那么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已经被娘家摆布得老是认为别无选择了,然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来摆布他。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苦莎出世了,一年后我的病情又被诊断出来,于是我们争论的方式也改变了。或许是因为菲力不但对孩子,也对我,至少是对我的健康状况,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我们不再自以为是地为观念上的差异而争论不休,那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这样有关个人选择的事情就变得难以处理,像抽烟、吃小牛肉和戴象牙饰物一样,成了一种一旦上手就难以摆脱的负担。
这些日子,我们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比如,争论的不是我们对于纪律的不同态度,而是有关我答应多给苔莎看半小时电视的问题。结果,我们的意见差不多总是接近一致——或许是太爽快了一点,因为我们早已料到意见不一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努力使生活变得更轻松、更平稳。但我还是时时感到烦躁不安。说实话,我倒还是希望回到从前,菲力和我争吵,我则为自己辩解,至少自己确信自己是对的。而如今——比方说今天——我真无法断定为什么我非得背起娘家的责任。我决不会对菲力承认这一点,但我已经对这份责任感到厌烦了。我不想见到匡家人,特别是玛丽。每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不得不用全部的时间来避开脚下的地雷。
所以,或许是因为觉得对不起菲力,或许是因为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一直拖到第二天才告诉菲力,我们得在那儿过一夜——参加杜姨婆的葬礼。
为了那个该死的周末,菲力和我已经决定早早进城安排好住处,或许还带孩子们去逛逛动物园。临走前一天,就我们在哪儿过夜的问题,我们和我母亲还来了一番客客气气的争执。
"你真是太客气了,雯妮,"菲力在电话里向我母亲作着解释,"可我们已经在旅馆里订好房间了。"我在分机上偷听着他们的谈话,心中暗喜。是我叫他打这个电话,并找到这个借口的。
"什么旅馆?"我母亲问。
"一家汽车旅馆。"菲力撒了个谎,实际上我们是在凯悦大饭店订了房间。
"嗨,那太贵了呀!"我母亲说,"何必这么浪费钱呢?你们可以在我这儿过夜的嘛,有的是房间。"
菲力很有礼貌地回绝道:"不了,不了,说真的。那样太麻烦了。真的。"
"麻烦谁了?"我母亲说。
所以这会儿菲力正在我弟弟的房间里把孩子们安顿下来。以前每当我和菲力要去开医学会议时,就让她们待在这儿。说实话,有时我们只是说要去开医学会议,其实是回家干活,把孩子在身边时没法干完的家务活干完。
菲力决定让八岁的苦莎睡单人床,三岁的克利奥睡帆布床。
"这次轮到我睡床,"克利奥说,"外一婆说过的。"
"可是克利奥,"苔莎解释道,"你喜欢帆布床呀。"
"外-婆!"克利奥赶紧喊我母亲来给她当救兵,"外一婆!"
菲力和我待在我的堆满老式家具的房间里。打从结婚后,我就没在这儿住过。房间还跟我当姑娘那会儿一样,没什么变化,只不过里面的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特别干净:一张双人床,床腿和床架又粗又重;一张带圆镜的梳妆台,镶着拐木、橡木、树疤制成的薄本片和珍珠母。真怪,当初我怎么会讨厌这桌子,现在看起来,它做工精巧,还蛮不错的。我不知道我母亲以后是否肯留给我。
我发现我母亲在床底下放了一双中国式旧拖鞋,就是每只大拇指头上都有一个洞的那双。她什么也舍不得扔掉,兴许二十年后还用得着呢。苔莎和克利奥准又钻进储藏室翻箱倒柜,在旧玩具和废物箱中执拉挑拣了。拖鞋的旁边,随地乱放着洋娃娃衣服、水晶石王后冠和一只盖上有"我的秘藏"字样的粉红色塑料盒。她们甚至把我在六年级时自己做的滑稽的好莱坞式明星又挂到了门上,那上面还有用珠子拼出的我的名字"珍珠"呢。
"老天,"菲力故意用傻乎乎的口气说,"这肯定比汽车旅馆还棒。"我捶了一下他的大腿。他拍打着床上一对很不协调的客用枕巾。这对枕巾还是我们刚从唐人街搬到利奇蒙地区时,匡家送的圣诞礼物,也就是说,至少用了三十年了。
这时,苔莎和克利奥一路打闹着跑进我们的房间,嚷着要去动物园。菲力准备趁我到丁和花店去帮忙的时候带她们去。我母亲倒并没说一定要我去帮忙,只是简短地提到海伦舅妈早就离开花店忙着准备她的大宴去了——尽管花店里杂事一大堆,明天又要操办杜姨婆的葬礼。然后她提醒我,杜姨婆总是为我感到骄傲——在我娘家的词汇里,"骄傲"的意思跟"爱"差不多。然后她又建议我或许该早点去,挑个好看一点的花圈。
"我五点半回来。"我告诉菲力。
"我想去看非洲大象,"苔莎一屁股坐在我们的床上,然后扳着手指头算,"还有无尾熊、有刺的食蚁兽和座头鲸。"我老是弄不懂她从哪儿学来这套排列事物的癖好——从菲力那儿?从我这儿?还是从电视上?
"要说'请',"菲力提醒她,"再说,动物园里也不会有鲸。"
我转向克利奥,我有时担心她在自信的姐姐身边会变得畏畏缩缩。"那么你想看什么呢?"我轻轻问她。她盯着自己的脚尖,想了一会儿,最后回答说:
"随便。"
我回到罗斯巷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已经沉寂下来了。下午灼热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唐人街人行道两旁周末嘈杂的市声也沉静下去了,整条巷子变得十分冷清,光线灰蒙蒙的,几乎带点淡绿色。
街的右面还是那家老的理发店,是阿福开的,我注意到他还是在用电推子给顾客修剪络腮胡子。街的对面还是一连串的住家连店铺,其中一家专替顾客运送祖先纪念物到大陆,赚点服务费。街的尽头是一家算命店的前门,窗子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招牌,声称"数字最幸运,算命最吉祥",但挂在门上的牌子却写着,"暂停营业"。
我穿过那扇门的时候,黄色的窗帘沙沙作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她双手按在玻璃窗上,两眼死死地盯住我,神色忧郁。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没有反应。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是属于这儿的人。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离花店没几间门面的三福贸易公司,它的货架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瓷器和木雕的神像。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管这地方叫神仙店。它也卖佛教葬礼上用的那些东西,什么纸钱啦,纸珠宝啦,香烛啦,等等。
"嗨,珍珠!"是店主洪先生在跟我打招呼,叫我进去。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三福就是他的名字哩。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话里,三福就是"三次祝福"的意思,据我母亲——或者不如说,据她的香港顾客们说,"三福"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说"傻乎乎"。
我母亲曾说过,"我早就劝他改个名字,那样运气会更好些。可他说他的生意已经够好啦。"
"嗨,珍珠,"我一进门,洪先生就说,"我已经给你母亲准备了一些东西,明天葬礼上要用的。你替我带给她,好吗?"
"没问题啦。"他递给我一包软乎乎的东西。
我猜,这就是说,姨婆的葬礼将以佛教的方式举行。尽管她加入第一华人浸礼会已有好多年了,但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我母亲就不再参加活动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姨婆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其他信仰,那倒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能消灾降福的迷信仪式她都坚信不疑。以前每当进她的屋子,我总是爱玩她的祭坛,一个红红的小寺庙,里面摆着中国神像,前面是一个仿铜的香炉,插满了点燃的香,旁边供奉着橘子、幸运牌香烟、飞机上出售的小瓶约翰尼牌红威士。这一切都很像降生在马槽上的基督的中国翻版。
此刻,我已经来到了花店门口。它坐落在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只有一个小型车库那么大,看上去又熟悉,又凄凉。红框店门上的防盗铁框已锈蚀不堪,玻璃窗上用中英文合写着"丁和花店"几个字,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因为花店坐落的地方太偏僻,看上去总是黑洞洞、局促促的,今天也还是那个样。
所以,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选择的地方实在不能说是闹市区,但看来她们干得还蛮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棒极了。毕竟,这么多年来,她们几乎没有赶过时髦,也没有使这地方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我打开门,铃声叮当作响。一股刺鼻的扼子花香扑面而来,这种气味总是使我联想到殡仪馆。室内光线幽暗,只有一支日光灯管吊在现金出纳机上方,我母亲就在那儿,她站在一只小脚凳上,以便能从柜台上照看到外面,鼻梁上架着一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老花眼镜。
她正在用中文打电话,话说得飞快,一面不耐烦地打手势叫我进去等着。她的头发从后脑直垂下来打成一个结,一丝不乱。今天,这个纽结由于加上了一鬏假发而变得更加浓密,她管这假发叫"马尾巴",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戴上它。
实际上,凭她那尖声的大嗓门和一连串否定词"勿一勿一勿",我就能断定她正在用上海话,而不是用普通话踉对方争论著。这就严重了。争论的对象很像是附近的一位鲜花供应商。我母亲一面按着计算器上的数字,一面大声地报着计算结果,好像这些数字就是法典。她按了一下现金出纳机上"停止营业"的按钮,抽屉一弹出,她就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发票,劈里啪啦地用肘子猛地把它掀开,然后报出一连串数字。
"勿!勿!勿!"她毫不让步。
这个现金出纳机通常被用来存放一些杂物,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出纳机已经坏了。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初次买下这房子和所有家产时,她们马上就发现,每当交易额加在一起里面出现一个"9"字,整个出纳机就卡住不动了。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出纳机。我母亲对我解释道,这是为了"防盗"。一旦她们遭劫(这类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强盗只能抢走小抽屉里的四个美元和一堆小钱。大笔的钱放在柜台底下一把破茶壶里,那茶壶放在一个少了插头的电炉上,壶嘴已经摔断过两次,是用胶水勉强粘上去的。我猜,她们想没有人会在抢劫商店时想到要一杯冷茶的。
有一次我对我母亲和海伦舅妈说,强盗决不会相信店里只有四个美元的。我认为她们至少得放二十个美元在现金出纳机里,这计谋才行得通。但我母亲认为二十美元给强盗太多了。海伦舅妈也说要费那么多钱她会"急出病"来的——既然如此,要这计谋干吗呢?
当时,我很想自己出二十美元来证明我的观点。但转念一想,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此刻当我环顾店堂时,我想,也许她们是对的。谁会跑到这儿来抢几个比公共汽车票钱多不了多少的钱呢?这地方凭它的老样子就能防盗。
店堂里还是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地面已经被磨得又滑又亮。柜台上铺着同样的装饰纸,两边是绿白相间的竹叶格子花,上面是木纹纸。甚至连我母亲正在用的电话机也还是同一架老式的黑机子,带圆盘的拨号盘,话筒线是棉包线制的,不能伸缩,也不会卷起来。那么多年来,石灰墙壁已经泛黄,斑驳不堪,1989年的地震又给它增加了裂缝。总之,这地方整个看起来把蜘蛛网的零落和腐叶土的霉味全占了。
"好,好。"我听到母亲说。看来她已经和那位供应商达成了妥协。终于,她搁下了话筒。尽管我们从圣诞节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但我们还是没有拥抱和亲吻,而去看菲力的双亲或他的朋友时,我们通常是要这么做的。母亲从柜台边走了过来,口中嘟哝着,"你想得到吗?这家伙居然骗我!想要我付一笔额外的运费。"她指指脚下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铅丝、透明胶纸和一些绿的蜡光纸。"上星期他忘了送来,这可不是我的错。"
"多少额外的费用?"我问。
"三美元!"她嚷道。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我母亲会为这几个美元而大动肝火。
"算了吧,不过三个美元嘛——"
"我倒不在乎这几个钱!"母亲气冲冲地说,"他在骗我,这是不对的。上个月,他也想再加一笔额外的费用。"我想她准又要开始跟我大讲特讲她上个月发生的战斗了。忽然,门口出现了两个穿着体面的金发女子,正朝里面东张西瞧。
"开开门好吗?你俩谁会说英语吗?"其中一个用德克萨斯口音问。
我母亲顿时满脸堆笑,连连点头,做手势叫她们进来。"请进,请进。"
"啊,不麻烦你们了,"其中一个说,"你能告诉我们幸运饼干店在哪儿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母亲的脸已经拉下来了,她连连摇头,说:"听不懂,不会说英语。"
"你干吗这么说呀?"那两个女人转身走入巷子时我不禁问道,"想不到你这样讨厌外地游客。"
"不是讨厌外地游客,"她说,"那饼干店的女人有一回对我很凶,我干吗给她介绍生意?"
"这里的生意怎么样?"我有意把话头岔开,以免这场谈话马上变成对那个住在街另一头的饼干店的女人的全面攻击。
"要命啦!"她说着,指指店里的存货。"这么多生意真把我忙死啦。你瞧,光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干了这么多。"
我看看周围,没有流行的插花,也没有标有拉丁文名字的进口货。我母亲打开通向冷藏室的玻璃门,那儿以前是放苏打水和啤酒的。
"瞧见了不?"她说着,给我看满满一货架用康乃馨制成的别在钮孔上的花和胸花,全都整整齐齐地按颜色深浅排列成行,有白的、粉红的,还有大红的,毫无疑问,是准备今晚给我们大家戴的。
"还有这个。"她接着说。第二个架子上塞满了乳白色的玻璃花瓶,每一只都只放一朵含苞的玫瑰、一片棕榈叶、一些满天星花。这类插花可以送给动手术住院的亲人。当你很久不去探望,不知道病人是否还在住院时,送这类花最合适。我父亲刚进医院那会儿和临死以前就收到过不少这类花。"行俏得很。"我母亲说。
"我还做了这个,"她说着,指指最底下的一个架子,里面有半打供桌上摆设用的装饰花,"有些是今晚用的,还有些是为一个退休告别宴会做的。"我母亲解释道。大概是见我脸上的表情一般,为了使我加深印象,她又加了一句,"是威尔斯法阁的副经理订做的。"
她又领我走了一圈,看了放在花店其他角落里她亲手做的工艺品。沿墙排着许多葬礼上用的大花圈。"怎么样?"她等着听我的称赞。我一向觉得花圈既恐怖又悲哀,就像扔晚了的救生圈,只能作装饰用。
"很漂亮。"我说。
现在她把我领到她最得意最骄傲的所在。花店的前半间是整个花店唯一每天能有几小时透进几缕阳光的地方,我母亲把这里称之为"长期订户",里面栽着黄薛树、橡胶树、矮小的灌木和迷你柑橘。这些都配上红彩带,或是为开张志喜,或是祝生意兴隆的。
我母亲一向来总是为这些红彩带而自豪,她不写老一套的贺词,像"吉祥如意"、"福禄长寿"之类。所有用烫金中文字写的贺词都是我母亲自己发明的,表达了她本人对生与死、幸运与希望的看法,什么"头生子有头福"啦,"结婚双喜、三喜临门"啦,什么"新店开张、财气冲天"啦,"健康恢复、指日可待"啦。
我母亲声称,丁和花店这么多年来之所以生意兴隆,全靠了这些彩带和贺词。我想,她所说的生意兴隆,大概是指二十五年来回头客很多。只不过眼下,为羞怯的新娘和轻佻的新郎订花的越来越少,为病人、老人和死人订花的越来越多。
她孩子气似地笑一笑,然后捅捅我的胳膊。"来,带你去看看我为你做的花圈。"
我大吃一惊,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打开通向花店后间的门,里面黑得像地窖一般,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葬礼上常有的浓重的桅子花味道。我母亲摸索着拉电灯开关线,终于,屋子里一下子亮得刺眼,一只吊在天花板上的光秃秃的灯泡来回晃荡着,我眼前出现了恐怖的美——一排又一排的花圈闪闪发光,全是用白桅于花和黄菊花扎起来的,红飘带从花架子上垂下来,整个看上去就像天国的仪仗队。
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这要花多大的劳动啊!我想象着母亲用那双羊皮般粗糙的小手,忙乱地拉出散叶,穿进铅丝头,把每一朵花都扎到合适的位置上。
"这一个,"她指指第一排中间的一个花圈,它看上去和别的花圈没什么两样,"这一个是你的,我亲手写了挽词。"
"都写些什么呀?"我问。
我母亲的手指缓缓地在红飘带上移动着,一面用我所听不懂的中文念着,然后翻译给我听,"姨婆大人安息,天堂吉祥。您最喜欢的外甥女珍珠路易勃兰特及外甥女婿同悼。"
"噢,我差点忘了。"我把从三福店里拿来的那包东西递给她,"这是洪先生叫我给你的。"
我母亲剪断绳子,打开包裹,里面一大叠纸钱,想来是烧给姨婆做天堂的买路钱的。
"想不到你还信这玩艺儿。"我说。
"什么相信,"我母亲说,"这是尊敬。"然后她的口气又缓和下来,"这里有一亿美元纸钱。唉!她真是位好太太。"
"从这边走吧。"我说着,当我们踏上通向宴会厅的楼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珍珠!菲力!你们来了。"是我表姐玛丽在喊我。打两年前她和她丈夫社搬到洛杉矶去以后,我就没见过她。我们等玛丽穿过宴会厅拥挤的人群。她直冲向我们,给我一个吻,然后摸摸我的脸,放声大笑,笑她给我带来的窘态。
"你看上去棒极了!"她告诉我,然后瞧瞧菲力,"真的,你俩都不错。气色挺好的。"
玛丽比我大半岁,今年该有四十一了。她化了浓妆,戴了假睫毛,头发卷成蓬松的一团。一条银狐长围巾老从她的肩上滑下来,她拉了三次,然后笑着说,"杜给我买了这老古董当圣诞礼物,讨厌死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讨厌,既然我们已经进了饭店。但玛丽就喜欢这样,她是两家孩子中的老大,对她来说,显示自己高人一头,总是最重要的。
"珍妮芬,迈克尔!"她喊道,打了个响指,"过来,跟姨父姨妈问声好。"她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拉到身边,紧抱了一下。"来吧,怎么说?"他们不情愿地看看我们,嘴里咕哝了几句,勉强点了点头。
珍妮芬已经长得很丰满,眼圈用眉笔描过,显得又小又凶,她的... -->>
每当我母亲跟我说话,一开头总像跟我吵嘴似的。
上星期她打电话给我,劈头就说,"珍珠啊——你非去不可,没二话好说的。"好大一会,我才明白她打电话的原由:海伦舅妈邀请一家子去参加我表弟宝宝的订婚晚会。
所谓"一家子"指的是匡家和路易斯家。匡家有海伦舅妈、亨利舅舅、玛丽、弗兰克,再加上宝宝。而路易斯家呢,现在实际上只剩下我和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去世了,而我弟弟塞缪尔现在新泽西。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别人就把我们看作"一家子",尽管匡家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海伦舅妈的前夫是我母亲的哥哥,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去世了。
说起我的表弟宝宝,他的本名是罗杰。但从小全家就叫他宝宝——宝宝在中文里是"乖孩子"的意思——后来就这么叫开了,因为他是个哭宝宝,我舅舅和舅妈一进门,他就哇哇大哭,说别的孩子惹他。现在他虽已三十一岁了,大家还是拿他当小孩看,还是要惹他。
"宝宝?他怎么又开订婚晚会了?"我说,"这是他第三次结婚了吧?"
"第四次了!"我母亲说,"上次没结成,我们送礼后不久就吹了。当然,这次海伦没说是订婚晚会,她只说是为玛丽搞一次大团圆。"
"玛丽也来了?"我问道。玛丽和我不光是表姐妹,还有另一层关系,她嫁给了杜楚,杜楚是我丈夫菲力勃兰特在医学院里的同学。说起来,十六年前,我和菲力还是经她介绍才认识的呢。
"玛丽要来,她丈夫和孩子们也来,"我母亲说,"下星期从洛杉矶直飞这儿。来不及买优待票了。买全额票,想不到吧?"
"下星期?"我一面说,一面找着借口,"现在通知我们临时改变计划好像晚了点,我们本来打算去——"
"海伦舅妈已经把你们算进去了。在水龙饭店设宴——要摆五桌咧!你们要是不去,一半的桌子都要空着了。"
我想象着海伦舅妈那样子,又矮又胖,缩得只有桌子腿那么高了。"另外还有些什么人去?"
"多着咧,都是些大人物。"我母亲说"大人物"这几个字的口气,好像在提起她不喜欢的人。"当然,她也会告诉人家说宝宝和他的未婚妻也要去。于是大家就都会问她,'未婚妻?宝宝又有新的未婚妻了?'然后,她就会说,'噢,我倒忘了。本来是想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的。可别说出去哟。'"
我母亲哼了一声。"她就是爱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这事。所以呀,你得带上一件礼物,也给她来个惊喜。上次你买了什么?"
"给宝宝和他的那位女生?我忘了,大概是一盒糖果。"
"他们吹了以后,他有没有送回来?"
"好像没有。我记不得了。"
"瞧!这就是匡家人的作风。这次可别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宴会前两天,我又接到了母亲打来的一个电话。
"听着,现在要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听她的口气,好像我犯了什么过错似的。然后她告诉我,杜姨婆去世了,享年九十七岁。我对这个消息倒并不感到惊讶,我还以为她早就去世了呢。
"她给你留了些好东西,"我母亲说,"这个周末你可以来拿走。"
杜姨婆实际上只是跟海伦有点血缘关系,是她父亲的同父异母姐妹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但我记得,是我母亲一直来在帮助照料杜姨婆。她每星期帮她清一次垃圾;每当收到印着老太太姓名的"百万美元"赌金独得券时,她就劝老太太别上当去订那些杂志;她还一次又一次地跑加州医药卫生当局,为杜姨婆申请老年医药费补助。
多年来,我母亲总是向我抱怨,说海伦不干这些事,倒要她来干。我母亲老是说"海伦,她呀,甚至提都没提起"。有一次,——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打断了她的唠叨,我说,"你干吗不踉海伦舅妈说你烦透了,而不再跟我唠叨呢?"这是菲力教我说的,以这种合情合理的方式,让我母亲明白究竟是什么使她活得这么累,以便她采取断然行动。
我这句话一出口,我母亲竟呆住了,她一脸惘然,哑口无言。打那以后,她再没向我唠叨过。事实上,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她没跟我讲过话。后来当我们之间又开口说话时,再也没提起过杜姨婆。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以为杜姨婆早就去世的缘故吧。
"那是怎么回事?"听到杜姨婆去世的消息,我尽量用平静中带点震惊的口气问,"是中风?"
"是车祸。"我母亲说。
显然,杜姨婆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精力充沛、身体康健的。出事那天,她当时搭乘的1号加州公共汽车,为了闪避一辆我母亲称之为"一群疯小子驾驶的改装高速车"突然打出的停车信号灯,而倾翻在路边。杜姨婆一个趔趄,倒在座位中间的过道上。当然,我母亲马上赶到医院去看她。医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只发现一些擦伤的青肿块。但杜姨婆说她来不及等医生来找出她早已知道的毛病,于是要我母亲写下她的遗嘱,吩咐后事,那张用了三十年的有节子的沙发给谁,黑白电视机给谁,等等等等。就在当天晚上,她死于未经查明的脑震荡。海伦本打算第二天去看望她,但已经太晚了。
"宝宝罗杰说我们应该起诉,要求赔偿一百万元。"我母亲说,"你想得到吗?动这种念头。杜姨婆临死的时候,他居然不哭,还想从死人身上赚钱!哼!我干吗还告诉他杜姨婆给他留了两盏灯?也许我该故意忘了这事。"
我母亲停了一会,又说:"她真是位好太太,已经订了十四个花圈。"然后她又放低声音说,"当然,每个都给八折优惠。"
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在唐人街罗斯巷合开了一家"丁和花店"。她俩是在大约二十五年前动起做卖花生意的念头的,当时,我父亲刚去世,海伦舅妈又丢了工作。花店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弥补天灾人祸的一个梦想。
我母亲用第一华人浸礼教会给的一笔捐款做花店的本钱,我父亲生前是该教会的本堂助理牧师。海伦舅妈用的是她在另一家花店工作期间的积蓄,她是在那家花店学会做卖花生意,又是在那里被解雇的。海伦舅妈自己说,她是因为"太老实"而被解雇的。但我母亲猜想,海伦舅妈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老是替顾客省钱,劝他们买最便宜的花。
"有时我真后悔婚后进入了一个中国家庭。"菲力听说我们不得不从圣何塞的家中出发,去远在百里之外的旧金山,而且逢周末足球赛交通更加拥挤时,便忍不住这样说。尽管婚后十五年来,他渐渐真诚地喜欢上我母亲了,但对她的不少要求还是有些恼火。再说,从医院下班后与一个大家庭共度周末,决不是他喜欢的度假方式。
"你是说我们非去不可了?"他心不在焉地说,一面忙着玩一个刚装进他的笔记本电脑的新软件。他按了一个键,"成功了!"他对着屏幕喊道,手舞足蹈起来。菲力今年四十三岁,他那一头粗硬的灰色头发往往使人感到难以接近。但这会儿,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一个正在玩玩具战舰的小孩。
我假装也正忙着,埋头啃一段难懂的文章。三个月前,我在本地学区得到了一个治疗语言障碍的门诊医生的职位。我对这份工作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但同时又暗暗担心可能错过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念头都是我母亲塞进我脑袋的。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她,说我战胜了另外两个申请同一职位的人而被选中时,我母亲说:"两个?就两个人要这份工作?"
这时菲力从电脑上探起身,留心我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在担心我的多发性硬化症,我们把它称之为我的"健康状况",这病虽还没有到使我全身虚弱的地步,但使我动不动就感到疲劳。"这个周末将会过得很紧张,"他说,"再说,我觉得你也受不了你的表弟宝宝,更何况玛丽也要去那儿。我的天,这下可好了。"
"嗯。"
"那么你是非去不可了?"
"嗯-哼。"
他叹了口气。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结婚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有关我的娘家、我的责任的话题。因为我们的争吵往往是由这个话题引出的。我们刚结婚的那会儿,菲力老是说我无论干什么总爱盲目地担心和内疚。我则反唇相讥说他自私,我说,人活著有时总得干一点不痛快或不方便的事。然后他就说,我们非那么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已经被娘家摆布得老是认为别无选择了,然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来摆布他。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苦莎出世了,一年后我的病情又被诊断出来,于是我们争论的方式也改变了。或许是因为菲力不但对孩子,也对我,至少是对我的健康状况,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我们不再自以为是地为观念上的差异而争论不休,那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这样有关个人选择的事情就变得难以处理,像抽烟、吃小牛肉和戴象牙饰物一样,成了一种一旦上手就难以摆脱的负担。
这些日子,我们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比如,争论的不是我们对于纪律的不同态度,而是有关我答应多给苔莎看半小时电视的问题。结果,我们的意见差不多总是接近一致——或许是太爽快了一点,因为我们早已料到意见不一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努力使生活变得更轻松、更平稳。但我还是时时感到烦躁不安。说实话,我倒还是希望回到从前,菲力和我争吵,我则为自己辩解,至少自己确信自己是对的。而如今——比方说今天——我真无法断定为什么我非得背起娘家的责任。我决不会对菲力承认这一点,但我已经对这份责任感到厌烦了。我不想见到匡家人,特别是玛丽。每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不得不用全部的时间来避开脚下的地雷。
所以,或许是因为觉得对不起菲力,或许是因为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一直拖到第二天才告诉菲力,我们得在那儿过一夜——参加杜姨婆的葬礼。
为了那个该死的周末,菲力和我已经决定早早进城安排好住处,或许还带孩子们去逛逛动物园。临走前一天,就我们在哪儿过夜的问题,我们和我母亲还来了一番客客气气的争执。
"你真是太客气了,雯妮,"菲力在电话里向我母亲作着解释,"可我们已经在旅馆里订好房间了。"我在分机上偷听着他们的谈话,心中暗喜。是我叫他打这个电话,并找到这个借口的。
"什么旅馆?"我母亲问。
"一家汽车旅馆。"菲力撒了个谎,实际上我们是在凯悦大饭店订了房间。
"嗨,那太贵了呀!"我母亲说,"何必这么浪费钱呢?你们可以在我这儿过夜的嘛,有的是房间。"
菲力很有礼貌地回绝道:"不了,不了,说真的。那样太麻烦了。真的。"
"麻烦谁了?"我母亲说。
所以这会儿菲力正在我弟弟的房间里把孩子们安顿下来。以前每当我和菲力要去开医学会议时,就让她们待在这儿。说实话,有时我们只是说要去开医学会议,其实是回家干活,把孩子在身边时没法干完的家务活干完。
菲力决定让八岁的苦莎睡单人床,三岁的克利奥睡帆布床。
"这次轮到我睡床,"克利奥说,"外一婆说过的。"
"可是克利奥,"苔莎解释道,"你喜欢帆布床呀。"
"外-婆!"克利奥赶紧喊我母亲来给她当救兵,"外一婆!"
菲力和我待在我的堆满老式家具的房间里。打从结婚后,我就没在这儿住过。房间还跟我当姑娘那会儿一样,没什么变化,只不过里面的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特别干净:一张双人床,床腿和床架又粗又重;一张带圆镜的梳妆台,镶着拐木、橡木、树疤制成的薄本片和珍珠母。真怪,当初我怎么会讨厌这桌子,现在看起来,它做工精巧,还蛮不错的。我不知道我母亲以后是否肯留给我。
我发现我母亲在床底下放了一双中国式旧拖鞋,就是每只大拇指头上都有一个洞的那双。她什么也舍不得扔掉,兴许二十年后还用得着呢。苔莎和克利奥准又钻进储藏室翻箱倒柜,在旧玩具和废物箱中执拉挑拣了。拖鞋的旁边,随地乱放着洋娃娃衣服、水晶石王后冠和一只盖上有"我的秘藏"字样的粉红色塑料盒。她们甚至把我在六年级时自己做的滑稽的好莱坞式明星又挂到了门上,那上面还有用珠子拼出的我的名字"珍珠"呢。
"老天,"菲力故意用傻乎乎的口气说,"这肯定比汽车旅馆还棒。"我捶了一下他的大腿。他拍打着床上一对很不协调的客用枕巾。这对枕巾还是我们刚从唐人街搬到利奇蒙地区时,匡家送的圣诞礼物,也就是说,至少用了三十年了。
这时,苔莎和克利奥一路打闹着跑进我们的房间,嚷着要去动物园。菲力准备趁我到丁和花店去帮忙的时候带她们去。我母亲倒并没说一定要我去帮忙,只是简短地提到海伦舅妈早就离开花店忙着准备她的大宴去了——尽管花店里杂事一大堆,明天又要操办杜姨婆的葬礼。然后她提醒我,杜姨婆总是为我感到骄傲——在我娘家的词汇里,"骄傲"的意思跟"爱"差不多。然后她又建议我或许该早点去,挑个好看一点的花圈。
"我五点半回来。"我告诉菲力。
"我想去看非洲大象,"苔莎一屁股坐在我们的床上,然后扳着手指头算,"还有无尾熊、有刺的食蚁兽和座头鲸。"我老是弄不懂她从哪儿学来这套排列事物的癖好——从菲力那儿?从我这儿?还是从电视上?
"要说'请',"菲力提醒她,"再说,动物园里也不会有鲸。"
我转向克利奥,我有时担心她在自信的姐姐身边会变得畏畏缩缩。"那么你想看什么呢?"我轻轻问她。她盯着自己的脚尖,想了一会儿,最后回答说:
"随便。"
我回到罗斯巷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已经沉寂下来了。下午灼热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唐人街人行道两旁周末嘈杂的市声也沉静下去了,整条巷子变得十分冷清,光线灰蒙蒙的,几乎带点淡绿色。
街的右面还是那家老的理发店,是阿福开的,我注意到他还是在用电推子给顾客修剪络腮胡子。街的对面还是一连串的住家连店铺,其中一家专替顾客运送祖先纪念物到大陆,赚点服务费。街的尽头是一家算命店的前门,窗子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招牌,声称"数字最幸运,算命最吉祥",但挂在门上的牌子却写着,"暂停营业"。
我穿过那扇门的时候,黄色的窗帘沙沙作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她双手按在玻璃窗上,两眼死死地盯住我,神色忧郁。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没有反应。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是属于这儿的人。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离花店没几间门面的三福贸易公司,它的货架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瓷器和木雕的神像。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管这地方叫神仙店。它也卖佛教葬礼上用的那些东西,什么纸钱啦,纸珠宝啦,香烛啦,等等。
"嗨,珍珠!"是店主洪先生在跟我打招呼,叫我进去。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三福就是他的名字哩。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话里,三福就是"三次祝福"的意思,据我母亲——或者不如说,据她的香港顾客们说,"三福"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说"傻乎乎"。
我母亲曾说过,"我早就劝他改个名字,那样运气会更好些。可他说他的生意已经够好啦。"
"嗨,珍珠,"我一进门,洪先生就说,"我已经给你母亲准备了一些东西,明天葬礼上要用的。你替我带给她,好吗?"
"没问题啦。"他递给我一包软乎乎的东西。
我猜,这就是说,姨婆的葬礼将以佛教的方式举行。尽管她加入第一华人浸礼会已有好多年了,但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我母亲就不再参加活动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姨婆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其他信仰,那倒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能消灾降福的迷信仪式她都坚信不疑。以前每当进她的屋子,我总是爱玩她的祭坛,一个红红的小寺庙,里面摆着中国神像,前面是一个仿铜的香炉,插满了点燃的香,旁边供奉着橘子、幸运牌香烟、飞机上出售的小瓶约翰尼牌红威士。这一切都很像降生在马槽上的基督的中国翻版。
此刻,我已经来到了花店门口。它坐落在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只有一个小型车库那么大,看上去又熟悉,又凄凉。红框店门上的防盗铁框已锈蚀不堪,玻璃窗上用中英文合写着"丁和花店"几个字,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因为花店坐落的地方太偏僻,看上去总是黑洞洞、局促促的,今天也还是那个样。
所以,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选择的地方实在不能说是闹市区,但看来她们干得还蛮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棒极了。毕竟,这么多年来,她们几乎没有赶过时髦,也没有使这地方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我打开门,铃声叮当作响。一股刺鼻的扼子花香扑面而来,这种气味总是使我联想到殡仪馆。室内光线幽暗,只有一支日光灯管吊在现金出纳机上方,我母亲就在那儿,她站在一只小脚凳上,以便能从柜台上照看到外面,鼻梁上架着一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老花眼镜。
她正在用中文打电话,话说得飞快,一面不耐烦地打手势叫我进去等着。她的头发从后脑直垂下来打成一个结,一丝不乱。今天,这个纽结由于加上了一鬏假发而变得更加浓密,她管这假发叫"马尾巴",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戴上它。
实际上,凭她那尖声的大嗓门和一连串否定词"勿一勿一勿",我就能断定她正在用上海话,而不是用普通话踉对方争论著。这就严重了。争论的对象很像是附近的一位鲜花供应商。我母亲一面按着计算器上的数字,一面大声地报着计算结果,好像这些数字就是法典。她按了一下现金出纳机上"停止营业"的按钮,抽屉一弹出,她就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发票,劈里啪啦地用肘子猛地把它掀开,然后报出一连串数字。
"勿!勿!勿!"她毫不让步。
这个现金出纳机通常被用来存放一些杂物,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出纳机已经坏了。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初次买下这房子和所有家产时,她们马上就发现,每当交易额加在一起里面出现一个"9"字,整个出纳机就卡住不动了。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出纳机。我母亲对我解释道,这是为了"防盗"。一旦她们遭劫(这类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强盗只能抢走小抽屉里的四个美元和一堆小钱。大笔的钱放在柜台底下一把破茶壶里,那茶壶放在一个少了插头的电炉上,壶嘴已经摔断过两次,是用胶水勉强粘上去的。我猜,她们想没有人会在抢劫商店时想到要一杯冷茶的。
有一次我对我母亲和海伦舅妈说,强盗决不会相信店里只有四个美元的。我认为她们至少得放二十个美元在现金出纳机里,这计谋才行得通。但我母亲认为二十美元给强盗太多了。海伦舅妈也说要费那么多钱她会"急出病"来的——既然如此,要这计谋干吗呢?
当时,我很想自己出二十美元来证明我的观点。但转念一想,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此刻当我环顾店堂时,我想,也许她们是对的。谁会跑到这儿来抢几个比公共汽车票钱多不了多少的钱呢?这地方凭它的老样子就能防盗。
店堂里还是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地面已经被磨得又滑又亮。柜台上铺着同样的装饰纸,两边是绿白相间的竹叶格子花,上面是木纹纸。甚至连我母亲正在用的电话机也还是同一架老式的黑机子,带圆盘的拨号盘,话筒线是棉包线制的,不能伸缩,也不会卷起来。那么多年来,石灰墙壁已经泛黄,斑驳不堪,1989年的地震又给它增加了裂缝。总之,这地方整个看起来把蜘蛛网的零落和腐叶土的霉味全占了。
"好,好。"我听到母亲说。看来她已经和那位供应商达成了妥协。终于,她搁下了话筒。尽管我们从圣诞节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但我们还是没有拥抱和亲吻,而去看菲力的双亲或他的朋友时,我们通常是要这么做的。母亲从柜台边走了过来,口中嘟哝着,"你想得到吗?这家伙居然骗我!想要我付一笔额外的运费。"她指指脚下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铅丝、透明胶纸和一些绿的蜡光纸。"上星期他忘了送来,这可不是我的错。"
"多少额外的费用?"我问。
"三美元!"她嚷道。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我母亲会为这几个美元而大动肝火。
"算了吧,不过三个美元嘛——"
"我倒不在乎这几个钱!"母亲气冲冲地说,"他在骗我,这是不对的。上个月,他也想再加一笔额外的费用。"我想她准又要开始跟我大讲特讲她上个月发生的战斗了。忽然,门口出现了两个穿着体面的金发女子,正朝里面东张西瞧。
"开开门好吗?你俩谁会说英语吗?"其中一个用德克萨斯口音问。
我母亲顿时满脸堆笑,连连点头,做手势叫她们进来。"请进,请进。"
"啊,不麻烦你们了,"其中一个说,"你能告诉我们幸运饼干店在哪儿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母亲的脸已经拉下来了,她连连摇头,说:"听不懂,不会说英语。"
"你干吗这么说呀?"那两个女人转身走入巷子时我不禁问道,"想不到你这样讨厌外地游客。"
"不是讨厌外地游客,"她说,"那饼干店的女人有一回对我很凶,我干吗给她介绍生意?"
"这里的生意怎么样?"我有意把话头岔开,以免这场谈话马上变成对那个住在街另一头的饼干店的女人的全面攻击。
"要命啦!"她说着,指指店里的存货。"这么多生意真把我忙死啦。你瞧,光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干了这么多。"
我看看周围,没有流行的插花,也没有标有拉丁文名字的进口货。我母亲打开通向冷藏室的玻璃门,那儿以前是放苏打水和啤酒的。
"瞧见了不?"她说着,给我看满满一货架用康乃馨制成的别在钮孔上的花和胸花,全都整整齐齐地按颜色深浅排列成行,有白的、粉红的,还有大红的,毫无疑问,是准备今晚给我们大家戴的。
"还有这个。"她接着说。第二个架子上塞满了乳白色的玻璃花瓶,每一只都只放一朵含苞的玫瑰、一片棕榈叶、一些满天星花。这类插花可以送给动手术住院的亲人。当你很久不去探望,不知道病人是否还在住院时,送这类花最合适。我父亲刚进医院那会儿和临死以前就收到过不少这类花。"行俏得很。"我母亲说。
"我还做了这个,"她说着,指指最底下的一个架子,里面有半打供桌上摆设用的装饰花,"有些是今晚用的,还有些是为一个退休告别宴会做的。"我母亲解释道。大概是见我脸上的表情一般,为了使我加深印象,她又加了一句,"是威尔斯法阁的副经理订做的。"
她又领我走了一圈,看了放在花店其他角落里她亲手做的工艺品。沿墙排着许多葬礼上用的大花圈。"怎么样?"她等着听我的称赞。我一向觉得花圈既恐怖又悲哀,就像扔晚了的救生圈,只能作装饰用。
"很漂亮。"我说。
现在她把我领到她最得意最骄傲的所在。花店的前半间是整个花店唯一每天能有几小时透进几缕阳光的地方,我母亲把这里称之为"长期订户",里面栽着黄薛树、橡胶树、矮小的灌木和迷你柑橘。这些都配上红彩带,或是为开张志喜,或是祝生意兴隆的。
我母亲一向来总是为这些红彩带而自豪,她不写老一套的贺词,像"吉祥如意"、"福禄长寿"之类。所有用烫金中文字写的贺词都是我母亲自己发明的,表达了她本人对生与死、幸运与希望的看法,什么"头生子有头福"啦,"结婚双喜、三喜临门"啦,什么"新店开张、财气冲天"啦,"健康恢复、指日可待"啦。
我母亲声称,丁和花店这么多年来之所以生意兴隆,全靠了这些彩带和贺词。我想,她所说的生意兴隆,大概是指二十五年来回头客很多。只不过眼下,为羞怯的新娘和轻佻的新郎订花的越来越少,为病人、老人和死人订花的越来越多。
她孩子气似地笑一笑,然后捅捅我的胳膊。"来,带你去看看我为你做的花圈。"
我大吃一惊,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打开通向花店后间的门,里面黑得像地窖一般,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葬礼上常有的浓重的桅子花味道。我母亲摸索着拉电灯开关线,终于,屋子里一下子亮得刺眼,一只吊在天花板上的光秃秃的灯泡来回晃荡着,我眼前出现了恐怖的美——一排又一排的花圈闪闪发光,全是用白桅于花和黄菊花扎起来的,红飘带从花架子上垂下来,整个看上去就像天国的仪仗队。
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这要花多大的劳动啊!我想象着母亲用那双羊皮般粗糙的小手,忙乱地拉出散叶,穿进铅丝头,把每一朵花都扎到合适的位置上。
"这一个,"她指指第一排中间的一个花圈,它看上去和别的花圈没什么两样,"这一个是你的,我亲手写了挽词。"
"都写些什么呀?"我问。
我母亲的手指缓缓地在红飘带上移动着,一面用我所听不懂的中文念着,然后翻译给我听,"姨婆大人安息,天堂吉祥。您最喜欢的外甥女珍珠路易勃兰特及外甥女婿同悼。"
"噢,我差点忘了。"我把从三福店里拿来的那包东西递给她,"这是洪先生叫我给你的。"
我母亲剪断绳子,打开包裹,里面一大叠纸钱,想来是烧给姨婆做天堂的买路钱的。
"想不到你还信这玩艺儿。"我说。
"什么相信,"我母亲说,"这是尊敬。"然后她的口气又缓和下来,"这里有一亿美元纸钱。唉!她真是位好太太。"
"从这边走吧。"我说着,当我们踏上通向宴会厅的楼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珍珠!菲力!你们来了。"是我表姐玛丽在喊我。打两年前她和她丈夫社搬到洛杉矶去以后,我就没见过她。我们等玛丽穿过宴会厅拥挤的人群。她直冲向我们,给我一个吻,然后摸摸我的脸,放声大笑,笑她给我带来的窘态。
"你看上去棒极了!"她告诉我,然后瞧瞧菲力,"真的,你俩都不错。气色挺好的。"
玛丽比我大半岁,今年该有四十一了。她化了浓妆,戴了假睫毛,头发卷成蓬松的一团。一条银狐长围巾老从她的肩上滑下来,她拉了三次,然后笑着说,"杜给我买了这老古董当圣诞礼物,讨厌死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讨厌,既然我们已经进了饭店。但玛丽就喜欢这样,她是两家孩子中的老大,对她来说,显示自己高人一头,总是最重要的。
"珍妮芬,迈克尔!"她喊道,打了个响指,"过来,跟姨父姨妈问声好。"她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拉到身边,紧抱了一下。"来吧,怎么说?"他们不情愿地看看我们,嘴里咕哝了几句,勉强点了点头。
珍妮芬已经长得很丰满,眼圈用眉笔描过,显得又小又凶,她的...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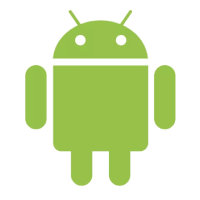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