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下文学 www.xxbxwx.net,男人的天堂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1
农村小老头笑着说,听了兄弟们的讲述,深受启发。其实,是非标准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无论如何优美动听的语言对它的描述都比不过心灵对它的感悟那样来得深刻,即所谓的触及心灵。
干巴巴的说教永远无法触及到人的心灵,往往要靠鲜活的生活才能搭起心与心交流的平台。兄弟们不妨耐心感悟一下我的讲述,看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收获。
讲述且从反季节大棚说起,说起来,反季节大棚算不上我们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步,这种调整早于村里人能够普遍地吃上白面馒头那天便已开始了。前面曾提及,这一天,刘老蔫儿让我们村比其他村提前了五年。
其实,就在大包干的当年,生活就已起了变化,而且变化是巨大的,恰如村里人所感叹的那样,这地咋象疯了似地一下子就长出了这么多粮食,任你敞开了肚皮去吃三两年也吃不完。
尽管这样,长期笼罩在村里人心里头的缺粮的阴影还是让人们不停地去多种粮食,因为吃饱肚皮似乎永远都是头等大事,有谁知道政策啥时会变,忍饥挨饿毕竟不是闹着玩的。万一?万一里尽是恐惧。真的有了万一,过去的人饿惯了兴许还能挺过去,现在这娃儿个个嫩藕似的可咋办?
然而,政策不仅没有变,反而听广播里报纸上说这政策一百年都不变,而且越说越坚决。现实也这样,所以,仅用了三两年的时间,家家户户早已粮满为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村里人的胆才真的壮了起来,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卖。卖?价格却远不如其他物资那样长得快,值不了多少钱,还是要卖,没办法,忍疼割爱也要卖。
终于有一天,村里人发现,肚皮算是吃饱了,料来三五年已无虞,口袋里却没有多少钱,远远跟不上诸如孩子上学之类开支加大的步伐。于是,村里头脑灵活机灵的人便尝试着种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时令货拿到集市上去卖,竟也赚了些钱。
我们村的土地多属沙性土壤,原也适合蔬菜水果之类作物的生长,种出来的菜果品质便出奇地好。村里人历来就有种菜果的习惯,见有人胆敢这么干,不仅没人管,而且赚了钱,便争相效仿。
渐渐地,种菜果的人多了,虽说物以稀为贵,东西多了便会不值钱,算起来却仍然比种粮食还要划算。
谁说中国的农民不会算账,如果你能够有幸听他们算一次,毛分厘计算之精确绝不会亚于一个自负学历的本科生。
同样地,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也丝毫不亚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阶层,尽管这种渴望有时候是盲目的,并因为盲目而固执,固执中甚至透着不可理喻的倔犟,却不可否认地蕴藏着巨大的不容忽视的热情,一旦得到启迪和开发,将会释放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样的做法显然与刘老蔫儿的要求背道而驰,必然为刘老蔫儿所不容。此时的刘老蔫儿正处于人生的巅峰,被数不清的荣誉光环笼罩着,但他的思路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阻碍,因为他自那个年代就养成了看报纸并善于从报纸上获取信息的习惯,所以他似乎总有跟他的荣誉一样数不清多的新想法新名词。
他别出新裁提出的“统一耕地、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浇水、统一喷药施肥、统一收获”所谓的“六统一”,在大包干的初期确起到了有效组织村民的作用,先后被乡里县里采纳并推广,后来连国家的报纸也做了连续报道。在乡村,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儿。
但以成方连片为前提的“六统一”很快便不再能够满足村里人的需求,村里头脑灵活的人认为,既然上面已经说了,放手让农民致富,你刘老蔫儿何必要管那么宽那么严,不是有位大人物说了嘛,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有本事无本事,致了富就叫真本事。致富才是硬道理,离了这个话题,管也没人肯听,大家都忙着赚钱,谁听你那些四五六瞎白话的大道理。
刘老蔫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既然上面已经肯定了的做法,那必然有要肯定的道理。才吃了几天饱饭,就变得这样没大没小没上没下,这还了得?刘老蔫儿越想越气,他决不会容许他们这样干。
可任他在村电台里喊破了嗓子,村里人依然我行我素。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所谓的教育,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惩罚手段。
尽管这样想着,刘老蔫儿还是从乡领导的讲话中感觉到了限制,妥善解决矛盾?什么叫妥善?说起来就是软呗,软皮蛋,明显的怕事怕担责任呗。既如此,为什么还要“六统一”?为什么还要把“六统一”纳入村干部的政绩来考核?我刘老蔫儿偏不信这个邪。
他决定杀鸡骇猴,这是他多少年来屡试不爽的一招。谁是鸡呢?便是刘阿龙家。
说起来,刘阿龙的父亲与刘老蔫儿属于同一枝的人,刘老蔫儿应该喊他一声叔。为什么要选他呢?因为刘老蔫儿始终认为,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须从我做起才最有说服力,要解决的当然首先是自己的堂叔。
另一个原因,恐怕是当时刘阿龙兄妹四人年龄都还小,最容易制服。办这类事必须要有把握,倘若把事情办砸,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越搞越糟。这是刘老蔫儿一惯的做法和经验。
对象选准了,目标就是清除他家的那块分明已经熟透了的却迟迟不肯收获的玉米地。那块玉米地恰好位于乡秋收检查组必经之路的路口,最为扎眼。这也算是他把对象定为刘阿龙家的一个原因吧。
要知道,当时县乡两级抓“催收催种”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按照事先确定的日期,层层检查落实,轻者通报批评,重则一年的工作一票否决。
刚开始还好,慢慢地村里人就不理解了:难道我们做了一辈子农民还不知道啥时收啥时种吗?
对,你真的不懂,刘老蔫儿斩钉截铁地说,你知道不误农事吗?知道?算你知道,可你知道庄稼熟了不收会养分倒流吗?养分倒流!这虽是个刘老蔫儿刚学来的名词,但他照样说的铿锵有力。
遇事先讲道理,讲过了多少遍仍不听,岂不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难道就因为你是我的堂叔?对,这分明是挑战,挑衅。——不知道这杆红旗是我老蔫儿亲自树起来的吗?决不能倒下,更不能给乡里的领导抹黑。这是他刘老蔫儿的作派。
所以,他不能熟视无睹了,他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就象当年抓计划生育那样果断。
提起计划生育,有必要在这里再啰嗦几句。计划生育毕竟不同于现在的倒茬,那可是被村里人认为是断子绝孙的事儿,他刘老蔫儿也想不通。所以工作总是时松时紧,不争气的是女人的肚子,吃了几天饱饭就憋足了劲地生,终于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既是硬仗,便要选择硬茬。这是他的信条。他当真就敢拆了族长儿子的房,在我们村,族长有着绝对的权威,但刘老蔫儿宣称自己有政府作后盾,谁敢与政府作对?果真有不少政府干部也参与了拆房。
我常想,应该感谢当时的法制还不十分健全,族长上告无门又迫于压力,便只能作罢,心里却是把刘老蔫儿的十八辈祖宗骂了个遍。
不过,这一招果然灵,见族长儿子的房都已经拆了,村里人便发现,原来这孩子并不是非生不可的,尽管倔犟的男人还是要生,女人们却先不干了,纷纷到乡计生站做了节育手续,有刘老蔫儿给她们作主,男人也奈何不了她们,并东凑西借地向村里交了超生罚款,要不然,自己的娃儿连户口都报不上,报不上户口就是黑人,那时候都这样叫,既然生了他(她),做父母的谁愿让自己的娃儿当黑人。
于是,刘老蔫儿如愿以偿地走到了全乡的前列,又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那年月,难事当真不少,刚结束了计划生育就要平坟,恰如族长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又要欺祖,当真不干人事了?
咱老蔫儿不与之计较,咱可不是那种没有政策水平的人,更不能不讲道理不讲策略,这一次他破例没有多讲道理,只简单地传达了文件便把自己父母的坟首先平了:这些坟占不了多少地,也影响不了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点儿,老蔫儿也想不通,但他还是按要求做了。
因为他做了,或许鉴于计划生育拆房的经验,待刘老蔫儿平了父母的坟之后的一觉醒来,村里的坟居然全平了。
想起这些,刘老蔫儿就想笑,这是足以让他一生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这些年终究不同于前些年了,这方面的意识明显弱化了,所以,在采取果断措施之前,刘老蔫儿最后一次到他叔家下了最后通牒。
他叔居然还是以忙为由左推右挡,分明不想倒茬,逼急了,竟然说,我知道你有能耐,看着办吧。
他叔向来就不是脆快的人,他不怕他叔,却冲他母老虎一样的婶发怵。发怵归发怵,相信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刘老蔫儿还是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又利用村电台反复讲了多遍,仍不见他叔有啥行动,这在前些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儿。
因为下午检查组就要来,他已经不能再退了,上午十点正的时候,他颇有点儿大将风度地把手一挥,早已等在院内的链轨车便随着他和村里的十几个干部出发了。
所谓的清除,并不是要帮他叔干活,而是用链轨车把地里的玉米秸推倒。
农村人都知道,玉米棒自立在地里的秸上往下掰还算容易,若推到了,就要难上何止几十倍。
值得庆幸的是,他叔也是能够看得开事理的人,并没有到现场阻拦,倒是几位围着看热闹的人说了几句“欺侮老实人”的俏皮话,立马被他派治安架到了场外。
如此顺利的局面,让他得意的脸上始终溢着笑意。岂不知被他架出去的人,气不过,特意跑去告知了他正在娘家为兄弟儿子过百岁的婶。待他正因为自己的杰作而兴冲冲地准备回家吃饭时,与边骂着“仗着有权强人”边赶来找他理论的婶碰了个正着。
女人扑上来就乱抓乱撕乱咬,要不是婆娘及时跑出来劝架,他险些被抓破了脸。
这可是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事情,他气炸了肺,不过,好男不跟女斗,但他还是转过脸来,指着女人骂道,就仗势欺你,怎么了,不要脸的臭女人!居然莫名其妙地底气不足,就因为女人?!
女人难怪叫母老虎,确实难斗:****的驴养的花样翻新地整整骂了他一个下午,直至晕死过去几次才被他叔软硬兼施地弄回家去。
而自家的婆娘却只会劝架,难道就不会骂?想着,他就来气,这死婆娘就是不会骂,而且劝架劝累了,负气回家,饭也不做,就知躺倒炕上赌气,害得他连中午饭都没吃上。
更可气的是,下午的检查,他自是又为全乡赢得了一个好名次,书记却在表扬他工作硬朗的同时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
书记指的肯定是他叔的事,他这么快就知道了,怎么会呢?难道他叔找过?不可能,他叔没有这样的能力。关于这点儿,他甚自信,那,书记又怎么知道呢?想不通就不想,这是他的格言。操,咱又为了什么,想想,这窝囊气生得实在太过不值。
但作为在村里有着绝对权威的支部书记,他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他必须要给这个臭婆娘一个处罚。如何处罚呢?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罚款,罚款也不是生产队的时候了,不交又咋办?
直到这时,刘老蔫儿才发觉,这世道真的变了。咱这岂不是在作茧自缚?他那时必定会涌上了这样的感叹,因为无可奈何。
不过,这难不倒他刘老蔫儿,他决定从村办工厂的利润里扣,不光他叔一家,还有另外几家,也必须扣。不能让这些自私自利的人沾到便宜,这是他做人的原则。
尽管他知道,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还有人要闹,但还是要扣。之前,他便这样做过,也有人闹过。但这正说明了人们对于分红的关注,是好事儿。刘老蔫儿就是这样想的。
兄弟们从前面的讲述中或许已经了解到,事实完全出乎刘老蔫儿所料,到那年年底,刘老蔫儿的那些村办企业已全面滑坡,工人留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恰如村里人所说,村办企业已没了人气。
2
人气,是非常被我们村里人看重的一种东西。没了人气,实际上就等于说“完了”。事实上,村办企业也已完全没了分红的能力。
但刘老蔫儿认为,这是事关他领导权威的大事,没有能力也要分,他就是要让那些反对者看看他的大气,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教育。对了,还有那些比如他的堂叔之流的该交罚款者,不是不交吗?不交就扣。仅为了这一点,红也是要分的。
说是分红,刘老蔫儿早已在村电台里沸沸扬扬宣传了好长时间,可钱又从哪里来呢?刘老蔫儿自有刘老蔫儿的招法,他凭着自己的影响,仅用一桌酒席的代价就从银行贷了十几万元。
我常想,这也算是银行管理的一个失误吧,要不是银行正嚷嚷着钱无处放似地支持乡村企业,刘老蔫儿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神通。哪里找如此便宜的事儿?
红总算是分了,却并没有出现象刘老蔫儿所期望的大家蜂拥着到村委会支取分红钱那样壮观的场面,因为村里人都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支了人家刘老蔫儿的钱就要受人管,自由远比受他的管制要强的多,更何况当年的菜果收入已经让不少的户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万元户,有谁还能再瞧得上这点儿分红款?所以有不少的户宁愿不去支,象我父亲就这样,直到我做了支书,才用这笔钱抵顶了村里的提留款。
分钱都没有人要,虽然对外又成了刘老蔫儿宣扬政绩的另一个话题,对内他却是明白的,这无疑是对他神圣权威的挑战,他不相信人心会变得这样快,便安排会计逐家逐户地送,虽然有几户又接受了他的分红,吃闭门羹却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分了三个月居然没有分完。
钱未及分完,麻烦却来了:银行主任一个愣怔酒醒了过来,心里的懊悔劲儿就别提了。据说他的领导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而且要免他的职,因为老蔫儿已经有许多笔贷款超期未还,所以就火烧火燎地索要贷款。
也怨不得老蔫儿赖账,因为钱早没了,至于何时能有,老蔫儿更是说不清。
老蔫儿说不清,主任就无计可施,只能抱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调离了我们乡。
新主任接受了老主任的教训,不再不遗余力地扶持老蔫儿。
其实,这里面也有个银行的经营问题——只要银行向企业投了足够数量的资金,银行就成了最不希望企业倒闭的企业共同体,就象吸大烟一样,明知继续投入有害,还总想着企业能活过来,即使有一丝活的希望,也只能去救,结果越救越深。据说,老主任事后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无论怎么说也已于事无补。
或许果如是,随着银行主任的调整,老蔫儿的企业快速地破产了,或者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叫做倒闭,因为地毕竟还是村集体的,债自然也是村集体的。
因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我们不再重复他因此而遭受的尴尬和挫折,单说他从此沉默了好长时间,待村里人再次注意他时,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他不仅没有象过去那样抓倒茬,而且有人发现他老婆也在默默地种菜果。据说,那年秋天县里检查倒茬,因为我们村的原因,乡里得了个倒数第一,书记破例拍着桌子骂了他,他只低着头不吭声,别提那样子有多惨了。
消息传开,村里人又开始可怜他。此时的他,已完全从村里人心目中的神位上走了下来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既是人,而且是管人的人,便要挨批评。
尽管他仍端着架子放不下,但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见了面,总要“哥”“叔”地喊他一声,他常常故意用鼻子“哼”一声便算应了,即使这样,村里人也能够原谅他,因为据说他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经常受到乡长书记的指责,而正因为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指责,我们村的菜果业才得以迅猛地发展起来。到乡里完全取消计划实行自由种植时,菜果业已成为我们村的主导产业,又走在了全乡的前列。
自由种植,并不等于撒手不管,而是要帮助农民探索出一条能够发家致富的路子。关于这一点儿,各级干部必须牢记。要帮着农民算账,要引导农民。县里的书记如是说,乡里的书记也如是说。
作为贯彻落实两级书记讲话的具体措施,自然便是跟当年抓乡村企业那样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办法,尽管这种办法并没有能够挽救乡村企业濒临倒闭的命运——也怪了,别人行,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并不缺鼻子少眼呀!纳闷归纳闷,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要出去,因为当时的乡村干部已经习惯了这种方法,只要遇到探索性的问题,这种方法就会被作为口号响亮地提出来并得到坚决的贯彻落实。
可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或许就因为出去的少了,不能够触及灵魂。既有人会问,就有人能给出答案,想想也是,原来如此呀!
所谓的“走出去学”,就是到一些先进的或者最先发展的地区去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和经典做法,目的是开阔眼界起引导作用。
据说,这种方法最先源于某位领导人关于放眼看世界的论述。当时,人们的不少行为都是必须要找到理论依据的,因为长期的封闭政策让人们明显变得缩手缩脚,没有理论依据的事若要干必然是要冒风险的,这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心态。
尽管这种方法后来被个别干部当成了公款游历名山大川的借口,但正是这种方法促进了乡村企业的发展。
关于乡村企业的发展,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即使这种探索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失败,它对于人们思想解放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至少传达了“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信息,无论最后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弥足珍贵的。实践证明,这些经验或教训的说服力远比十几年空洞的说教有力,我们村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儿。
“走出去学”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组织的。按照通常的做法,书记首先确定一个基调,然后由乡长带着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和管区的干部到外面去考察了十几天的时间,结果便是要而且必须要发展冬暖式大棚。
提及大棚,参与考察的人就不由自主地要热血沸腾:这东西太神奇了,冬天居然能长出新鲜的菜,收入也不错,一年上万元!
现实是,这些人的热情再高,再四处宣扬,却连村支书这一级也感动不了,尽管村支书们还是耐心地虽然有些倦怠地听完了他们神采飞扬的描绘——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再说了,我们一年平平稳稳也收入上万元,也不错了。
这是思想的问题,书记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些头脑不开窍的村支书也去看,直看到他们象当年发展乡村企业和兴修水利那样兴奋与忘我。
既然书记说了,就必须要去,格自然要低一点儿,由分管的副乡长带队。即便这样,乡财政也没钱,副乡长便说由各村自己带... -->>
1
农村小老头笑着说,听了兄弟们的讲述,深受启发。其实,是非标准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无论如何优美动听的语言对它的描述都比不过心灵对它的感悟那样来得深刻,即所谓的触及心灵。
干巴巴的说教永远无法触及到人的心灵,往往要靠鲜活的生活才能搭起心与心交流的平台。兄弟们不妨耐心感悟一下我的讲述,看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收获。
讲述且从反季节大棚说起,说起来,反季节大棚算不上我们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步,这种调整早于村里人能够普遍地吃上白面馒头那天便已开始了。前面曾提及,这一天,刘老蔫儿让我们村比其他村提前了五年。
其实,就在大包干的当年,生活就已起了变化,而且变化是巨大的,恰如村里人所感叹的那样,这地咋象疯了似地一下子就长出了这么多粮食,任你敞开了肚皮去吃三两年也吃不完。
尽管这样,长期笼罩在村里人心里头的缺粮的阴影还是让人们不停地去多种粮食,因为吃饱肚皮似乎永远都是头等大事,有谁知道政策啥时会变,忍饥挨饿毕竟不是闹着玩的。万一?万一里尽是恐惧。真的有了万一,过去的人饿惯了兴许还能挺过去,现在这娃儿个个嫩藕似的可咋办?
然而,政策不仅没有变,反而听广播里报纸上说这政策一百年都不变,而且越说越坚决。现实也这样,所以,仅用了三两年的时间,家家户户早已粮满为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村里人的胆才真的壮了起来,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卖。卖?价格却远不如其他物资那样长得快,值不了多少钱,还是要卖,没办法,忍疼割爱也要卖。
终于有一天,村里人发现,肚皮算是吃饱了,料来三五年已无虞,口袋里却没有多少钱,远远跟不上诸如孩子上学之类开支加大的步伐。于是,村里头脑灵活机灵的人便尝试着种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时令货拿到集市上去卖,竟也赚了些钱。
我们村的土地多属沙性土壤,原也适合蔬菜水果之类作物的生长,种出来的菜果品质便出奇地好。村里人历来就有种菜果的习惯,见有人胆敢这么干,不仅没人管,而且赚了钱,便争相效仿。
渐渐地,种菜果的人多了,虽说物以稀为贵,东西多了便会不值钱,算起来却仍然比种粮食还要划算。
谁说中国的农民不会算账,如果你能够有幸听他们算一次,毛分厘计算之精确绝不会亚于一个自负学历的本科生。
同样地,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也丝毫不亚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阶层,尽管这种渴望有时候是盲目的,并因为盲目而固执,固执中甚至透着不可理喻的倔犟,却不可否认地蕴藏着巨大的不容忽视的热情,一旦得到启迪和开发,将会释放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样的做法显然与刘老蔫儿的要求背道而驰,必然为刘老蔫儿所不容。此时的刘老蔫儿正处于人生的巅峰,被数不清的荣誉光环笼罩着,但他的思路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阻碍,因为他自那个年代就养成了看报纸并善于从报纸上获取信息的习惯,所以他似乎总有跟他的荣誉一样数不清多的新想法新名词。
他别出新裁提出的“统一耕地、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浇水、统一喷药施肥、统一收获”所谓的“六统一”,在大包干的初期确起到了有效组织村民的作用,先后被乡里县里采纳并推广,后来连国家的报纸也做了连续报道。在乡村,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儿。
但以成方连片为前提的“六统一”很快便不再能够满足村里人的需求,村里头脑灵活的人认为,既然上面已经说了,放手让农民致富,你刘老蔫儿何必要管那么宽那么严,不是有位大人物说了嘛,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有本事无本事,致了富就叫真本事。致富才是硬道理,离了这个话题,管也没人肯听,大家都忙着赚钱,谁听你那些四五六瞎白话的大道理。
刘老蔫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既然上面已经肯定了的做法,那必然有要肯定的道理。才吃了几天饱饭,就变得这样没大没小没上没下,这还了得?刘老蔫儿越想越气,他决不会容许他们这样干。
可任他在村电台里喊破了嗓子,村里人依然我行我素。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所谓的教育,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惩罚手段。
尽管这样想着,刘老蔫儿还是从乡领导的讲话中感觉到了限制,妥善解决矛盾?什么叫妥善?说起来就是软呗,软皮蛋,明显的怕事怕担责任呗。既如此,为什么还要“六统一”?为什么还要把“六统一”纳入村干部的政绩来考核?我刘老蔫儿偏不信这个邪。
他决定杀鸡骇猴,这是他多少年来屡试不爽的一招。谁是鸡呢?便是刘阿龙家。
说起来,刘阿龙的父亲与刘老蔫儿属于同一枝的人,刘老蔫儿应该喊他一声叔。为什么要选他呢?因为刘老蔫儿始终认为,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须从我做起才最有说服力,要解决的当然首先是自己的堂叔。
另一个原因,恐怕是当时刘阿龙兄妹四人年龄都还小,最容易制服。办这类事必须要有把握,倘若把事情办砸,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越搞越糟。这是刘老蔫儿一惯的做法和经验。
对象选准了,目标就是清除他家的那块分明已经熟透了的却迟迟不肯收获的玉米地。那块玉米地恰好位于乡秋收检查组必经之路的路口,最为扎眼。这也算是他把对象定为刘阿龙家的一个原因吧。
要知道,当时县乡两级抓“催收催种”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按照事先确定的日期,层层检查落实,轻者通报批评,重则一年的工作一票否决。
刚开始还好,慢慢地村里人就不理解了:难道我们做了一辈子农民还不知道啥时收啥时种吗?
对,你真的不懂,刘老蔫儿斩钉截铁地说,你知道不误农事吗?知道?算你知道,可你知道庄稼熟了不收会养分倒流吗?养分倒流!这虽是个刘老蔫儿刚学来的名词,但他照样说的铿锵有力。
遇事先讲道理,讲过了多少遍仍不听,岂不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难道就因为你是我的堂叔?对,这分明是挑战,挑衅。——不知道这杆红旗是我老蔫儿亲自树起来的吗?决不能倒下,更不能给乡里的领导抹黑。这是他刘老蔫儿的作派。
所以,他不能熟视无睹了,他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就象当年抓计划生育那样果断。
提起计划生育,有必要在这里再啰嗦几句。计划生育毕竟不同于现在的倒茬,那可是被村里人认为是断子绝孙的事儿,他刘老蔫儿也想不通。所以工作总是时松时紧,不争气的是女人的肚子,吃了几天饱饭就憋足了劲地生,终于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既是硬仗,便要选择硬茬。这是他的信条。他当真就敢拆了族长儿子的房,在我们村,族长有着绝对的权威,但刘老蔫儿宣称自己有政府作后盾,谁敢与政府作对?果真有不少政府干部也参与了拆房。
我常想,应该感谢当时的法制还不十分健全,族长上告无门又迫于压力,便只能作罢,心里却是把刘老蔫儿的十八辈祖宗骂了个遍。
不过,这一招果然灵,见族长儿子的房都已经拆了,村里人便发现,原来这孩子并不是非生不可的,尽管倔犟的男人还是要生,女人们却先不干了,纷纷到乡计生站做了节育手续,有刘老蔫儿给她们作主,男人也奈何不了她们,并东凑西借地向村里交了超生罚款,要不然,自己的娃儿连户口都报不上,报不上户口就是黑人,那时候都这样叫,既然生了他(她),做父母的谁愿让自己的娃儿当黑人。
于是,刘老蔫儿如愿以偿地走到了全乡的前列,又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那年月,难事当真不少,刚结束了计划生育就要平坟,恰如族长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又要欺祖,当真不干人事了?
咱老蔫儿不与之计较,咱可不是那种没有政策水平的人,更不能不讲道理不讲策略,这一次他破例没有多讲道理,只简单地传达了文件便把自己父母的坟首先平了:这些坟占不了多少地,也影响不了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点儿,老蔫儿也想不通,但他还是按要求做了。
因为他做了,或许鉴于计划生育拆房的经验,待刘老蔫儿平了父母的坟之后的一觉醒来,村里的坟居然全平了。
想起这些,刘老蔫儿就想笑,这是足以让他一生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这些年终究不同于前些年了,这方面的意识明显弱化了,所以,在采取果断措施之前,刘老蔫儿最后一次到他叔家下了最后通牒。
他叔居然还是以忙为由左推右挡,分明不想倒茬,逼急了,竟然说,我知道你有能耐,看着办吧。
他叔向来就不是脆快的人,他不怕他叔,却冲他母老虎一样的婶发怵。发怵归发怵,相信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刘老蔫儿还是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又利用村电台反复讲了多遍,仍不见他叔有啥行动,这在前些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儿。
因为下午检查组就要来,他已经不能再退了,上午十点正的时候,他颇有点儿大将风度地把手一挥,早已等在院内的链轨车便随着他和村里的十几个干部出发了。
所谓的清除,并不是要帮他叔干活,而是用链轨车把地里的玉米秸推倒。
农村人都知道,玉米棒自立在地里的秸上往下掰还算容易,若推到了,就要难上何止几十倍。
值得庆幸的是,他叔也是能够看得开事理的人,并没有到现场阻拦,倒是几位围着看热闹的人说了几句“欺侮老实人”的俏皮话,立马被他派治安架到了场外。
如此顺利的局面,让他得意的脸上始终溢着笑意。岂不知被他架出去的人,气不过,特意跑去告知了他正在娘家为兄弟儿子过百岁的婶。待他正因为自己的杰作而兴冲冲地准备回家吃饭时,与边骂着“仗着有权强人”边赶来找他理论的婶碰了个正着。
女人扑上来就乱抓乱撕乱咬,要不是婆娘及时跑出来劝架,他险些被抓破了脸。
这可是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事情,他气炸了肺,不过,好男不跟女斗,但他还是转过脸来,指着女人骂道,就仗势欺你,怎么了,不要脸的臭女人!居然莫名其妙地底气不足,就因为女人?!
女人难怪叫母老虎,确实难斗:****的驴养的花样翻新地整整骂了他一个下午,直至晕死过去几次才被他叔软硬兼施地弄回家去。
而自家的婆娘却只会劝架,难道就不会骂?想着,他就来气,这死婆娘就是不会骂,而且劝架劝累了,负气回家,饭也不做,就知躺倒炕上赌气,害得他连中午饭都没吃上。
更可气的是,下午的检查,他自是又为全乡赢得了一个好名次,书记却在表扬他工作硬朗的同时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
书记指的肯定是他叔的事,他这么快就知道了,怎么会呢?难道他叔找过?不可能,他叔没有这样的能力。关于这点儿,他甚自信,那,书记又怎么知道呢?想不通就不想,这是他的格言。操,咱又为了什么,想想,这窝囊气生得实在太过不值。
但作为在村里有着绝对权威的支部书记,他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他必须要给这个臭婆娘一个处罚。如何处罚呢?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罚款,罚款也不是生产队的时候了,不交又咋办?
直到这时,刘老蔫儿才发觉,这世道真的变了。咱这岂不是在作茧自缚?他那时必定会涌上了这样的感叹,因为无可奈何。
不过,这难不倒他刘老蔫儿,他决定从村办工厂的利润里扣,不光他叔一家,还有另外几家,也必须扣。不能让这些自私自利的人沾到便宜,这是他做人的原则。
尽管他知道,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还有人要闹,但还是要扣。之前,他便这样做过,也有人闹过。但这正说明了人们对于分红的关注,是好事儿。刘老蔫儿就是这样想的。
兄弟们从前面的讲述中或许已经了解到,事实完全出乎刘老蔫儿所料,到那年年底,刘老蔫儿的那些村办企业已全面滑坡,工人留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恰如村里人所说,村办企业已没了人气。
2
人气,是非常被我们村里人看重的一种东西。没了人气,实际上就等于说“完了”。事实上,村办企业也已完全没了分红的能力。
但刘老蔫儿认为,这是事关他领导权威的大事,没有能力也要分,他就是要让那些反对者看看他的大气,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教育。对了,还有那些比如他的堂叔之流的该交罚款者,不是不交吗?不交就扣。仅为了这一点,红也是要分的。
说是分红,刘老蔫儿早已在村电台里沸沸扬扬宣传了好长时间,可钱又从哪里来呢?刘老蔫儿自有刘老蔫儿的招法,他凭着自己的影响,仅用一桌酒席的代价就从银行贷了十几万元。
我常想,这也算是银行管理的一个失误吧,要不是银行正嚷嚷着钱无处放似地支持乡村企业,刘老蔫儿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神通。哪里找如此便宜的事儿?
红总算是分了,却并没有出现象刘老蔫儿所期望的大家蜂拥着到村委会支取分红钱那样壮观的场面,因为村里人都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支了人家刘老蔫儿的钱就要受人管,自由远比受他的管制要强的多,更何况当年的菜果收入已经让不少的户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万元户,有谁还能再瞧得上这点儿分红款?所以有不少的户宁愿不去支,象我父亲就这样,直到我做了支书,才用这笔钱抵顶了村里的提留款。
分钱都没有人要,虽然对外又成了刘老蔫儿宣扬政绩的另一个话题,对内他却是明白的,这无疑是对他神圣权威的挑战,他不相信人心会变得这样快,便安排会计逐家逐户地送,虽然有几户又接受了他的分红,吃闭门羹却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分了三个月居然没有分完。
钱未及分完,麻烦却来了:银行主任一个愣怔酒醒了过来,心里的懊悔劲儿就别提了。据说他的领导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而且要免他的职,因为老蔫儿已经有许多笔贷款超期未还,所以就火烧火燎地索要贷款。
也怨不得老蔫儿赖账,因为钱早没了,至于何时能有,老蔫儿更是说不清。
老蔫儿说不清,主任就无计可施,只能抱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调离了我们乡。
新主任接受了老主任的教训,不再不遗余力地扶持老蔫儿。
其实,这里面也有个银行的经营问题——只要银行向企业投了足够数量的资金,银行就成了最不希望企业倒闭的企业共同体,就象吸大烟一样,明知继续投入有害,还总想着企业能活过来,即使有一丝活的希望,也只能去救,结果越救越深。据说,老主任事后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无论怎么说也已于事无补。
或许果如是,随着银行主任的调整,老蔫儿的企业快速地破产了,或者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叫做倒闭,因为地毕竟还是村集体的,债自然也是村集体的。
因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我们不再重复他因此而遭受的尴尬和挫折,单说他从此沉默了好长时间,待村里人再次注意他时,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他不仅没有象过去那样抓倒茬,而且有人发现他老婆也在默默地种菜果。据说,那年秋天县里检查倒茬,因为我们村的原因,乡里得了个倒数第一,书记破例拍着桌子骂了他,他只低着头不吭声,别提那样子有多惨了。
消息传开,村里人又开始可怜他。此时的他,已完全从村里人心目中的神位上走了下来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既是人,而且是管人的人,便要挨批评。
尽管他仍端着架子放不下,但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见了面,总要“哥”“叔”地喊他一声,他常常故意用鼻子“哼”一声便算应了,即使这样,村里人也能够原谅他,因为据说他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经常受到乡长书记的指责,而正因为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指责,我们村的菜果业才得以迅猛地发展起来。到乡里完全取消计划实行自由种植时,菜果业已成为我们村的主导产业,又走在了全乡的前列。
自由种植,并不等于撒手不管,而是要帮助农民探索出一条能够发家致富的路子。关于这一点儿,各级干部必须牢记。要帮着农民算账,要引导农民。县里的书记如是说,乡里的书记也如是说。
作为贯彻落实两级书记讲话的具体措施,自然便是跟当年抓乡村企业那样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办法,尽管这种办法并没有能够挽救乡村企业濒临倒闭的命运——也怪了,别人行,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并不缺鼻子少眼呀!纳闷归纳闷,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要出去,因为当时的乡村干部已经习惯了这种方法,只要遇到探索性的问题,这种方法就会被作为口号响亮地提出来并得到坚决的贯彻落实。
可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或许就因为出去的少了,不能够触及灵魂。既有人会问,就有人能给出答案,想想也是,原来如此呀!
所谓的“走出去学”,就是到一些先进的或者最先发展的地区去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和经典做法,目的是开阔眼界起引导作用。
据说,这种方法最先源于某位领导人关于放眼看世界的论述。当时,人们的不少行为都是必须要找到理论依据的,因为长期的封闭政策让人们明显变得缩手缩脚,没有理论依据的事若要干必然是要冒风险的,这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心态。
尽管这种方法后来被个别干部当成了公款游历名山大川的借口,但正是这种方法促进了乡村企业的发展。
关于乡村企业的发展,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即使这种探索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失败,它对于人们思想解放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至少传达了“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信息,无论最后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弥足珍贵的。实践证明,这些经验或教训的说服力远比十几年空洞的说教有力,我们村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儿。
“走出去学”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组织的。按照通常的做法,书记首先确定一个基调,然后由乡长带着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和管区的干部到外面去考察了十几天的时间,结果便是要而且必须要发展冬暖式大棚。
提及大棚,参与考察的人就不由自主地要热血沸腾:这东西太神奇了,冬天居然能长出新鲜的菜,收入也不错,一年上万元!
现实是,这些人的热情再高,再四处宣扬,却连村支书这一级也感动不了,尽管村支书们还是耐心地虽然有些倦怠地听完了他们神采飞扬的描绘——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再说了,我们一年平平稳稳也收入上万元,也不错了。
这是思想的问题,书记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些头脑不开窍的村支书也去看,直看到他们象当年发展乡村企业和兴修水利那样兴奋与忘我。
既然书记说了,就必须要去,格自然要低一点儿,由分管的副乡长带队。即便这样,乡财政也没钱,副乡长便说由各村自己带...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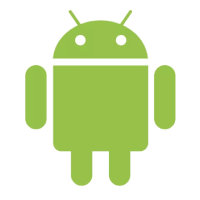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